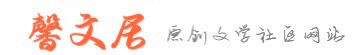骤雨。黄昏。普林斯顿的咖啡小屋。青荧荧的灯下,她的目光缓缓转向窗外的街道:“你看他们多么从容。”用的是易安居士《永遇乐》的语调。随着她的视线望去,但见白花花的街道如川,亮闪闪的车辆如鲫,这一刻,以及接踵而来的下一刻,唯独不见徒步的行人——行人都叫骤雨淋跑了;我始而愕然,继而陷入恍惚,悟不透她口中所谓“从容的他们”,确切指的是谁。
无人在场。刚才我们谈到了谁?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余英时……都是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华人前辈;当然也谈到了爱因斯坦,生前,晚年,爱翁常常在普林斯顿的街头闲逛,小小的个儿,大大的鼻梁,蓬松如狮的脑袋,锐利如鹰的目光,配上松松垮垮的衣服,往下看,还趿拉着一双破旧的拖鞋。爱因斯坦是20世纪的徽记,上帝的杰作,至今仍是文化圈不老的话题。他们,都已风流云散,都成明日黄花,仅留余韵。
余韵袅袅。蓦然回首,想起另一次隔案相对,我和她,在“文革”席卷神州的第六个岁尾,于古城长沙俯瞰湘江的一处茶楼。她有渊深的家世,三代以上,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座上客,两代以上,交游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截至她的上代,格局为之一变,伯父、叔父、舅父,以及三姑六姨,数得出的近亲,都乘桴浮于海,散作他乡之蓬了,只有那位留学欧美的父亲,贪恋沪上红尘,最终作了刘海粟、傅雷的密友,“反右”的漏网之鱼,“文革”的瓮中之鳖。那时,她对这一切讳莫如深,我只是隐隐约约风闻,以及闲谈中捕风捉影地猜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俩在一次半地下的文学沙龙中认识,缘于诗。诗真是个神妙的东西,往往一个词,一个字,就能令五内鼎沸,激情飞扬。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写了多少诗,我是把一辈子的诗心都掏光了,以至后来再没挤出过完整的一首。
那一天,她约我去寻贾太傅的故宅,说是就在长沙西区。兴冲冲渡江而去,穿街过巷,寻阡问陌,被问者多瞠目以对:这年头,还找什么假太傅真太傅!劳而无功,怅然而返,时近中午,就便登上了临江的茶楼。那一次我们触景生情,谈论起“文革”的荒腔走板,毁灭传统,毁灭学术,不啻毁灭生存的根……“你听说过陈寅恪、唐篔吗?”感慨之际,她忽然问我。摇头,我承认孤陋寡闻。她凄然一笑,不作解释,只是眼望天外,淡淡地说:“他们都走了。”
未久,她便离开长沙,返回上海,使用的妙策:称病。天可怜见,你禁这禁那,禁不了生病的自由!人能生病,是限制,也是反限制。人又说写诗的人是敏感的,我却是迟钝,迟钝到以为她是文科出身,如我,待听她说出回沪后闭门自修的计划,才恍悟她原来是牛顿、爱因斯坦的徒子徒孙。

她走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我读书的研究生院,我们又意外地碰头了。她来找陈封雄,陈寅恪的侄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资深编辑,我的导师之一。从封雄老师口里,才弄清她的家世,对于我,她是游行在历史云端的神龙,渺乎高哉,可望而不可即。也就在那次,她透露,年内要去美国读书。那个年头,国门在关闭多年后刚刚打开一条窄缝,有关系、有闯劲的青年蜂拥往外挤,她有着庞大的海外背景,岂能弃之不用——我为她感到庆幸。
说到我,也不是没有出国机会,但我既愚且倔,在一次短暂的海外游历之后,居然选择放弃。我宁愿守在中国,守着我的母语,守着我的一亩二分田。大千世界,人各有志。如是过了十年,彼此再度会面,是她回国探亲时,地点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那时她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切都处在玫瑰色的上升期。她送了我一幅写意的水彩,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一隅。我送了她两本自选随笔集,《少年中国》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座的还有新华社的数位同行,她是当然的主角,谈得最起劲的是异邦的风光,如何销魂餍心,乐不思蜀,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关系,帮助国内招商引资。后一个题目一出,立马搔到群体的痒处,人人献计献策,顽钝如我,也当场翻出几位地方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是我记者生涯的副产品。她是说到做到,事后果然和其中的一位取得联系,并且在纽约参与接待了该地的访美考察团。事情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不见下文——有下文又怎样?她就是个牵线的,桥一搭成,使命随之结束。
这一现的神龙后来又没了踪影,相忘于岁月,相忘于江湖。忽忽就到了21世纪,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又现身北京。自述此番不为探亲——事实上她已无亲可探,该走的都走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当年的豪气竟已烟消云散。说到专业,她坦言“文革”耽误得太多了,紧追猛追,再也追不回来,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科学是年轻人的乐园,像她这种年纪的学者,很难再有发展,只是凭惯性向前走,然后就,等待退休养老。“那么干脆回来。”我说。她笑了,笑容呈现苦涩:“回来?回哪儿去?你当我是揣着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蓦然一惊,醒悟韶华不再,机会不再,她和我已是踏遍千山后的倦客。
此番赴美,途经纽约,入住新泽西州的一家乡村旅店,前晚电话联络,第二天一早,她就驾车来接我。然后带我去纽约城,逛曼哈顿,逛唐人街,末了回到普林斯顿小镇,参观她所在的大学,以及爱因斯坦待过的高等研究院。途中,感觉她刻意回避家庭,听说她离异过两次,大不幸,无论西方东方,这都属隐私,尤其是女人。带着一份心照不宣的谨慎,彼此只谈国事、天下事,不谈自己。
晚餐是在一家中餐馆享用的,主人和她相熟。餐后天雨,半途中止散步,就近避入一家咖啡店。也好,三十多年的相识,三万里路相隔,一肚皮的话,正好唠唠。谈罢普林斯顿的名流,转入俗世男女,问起她日常来往的华人朋友,她说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位,一位是上海来的女士,旋风一般地嫁人,嫁人犹如谋生,最近嫁去了墨西哥,五十出头的人了,但愿是最后一嫁。一位也是上海来的,男士,干过这推销,那推销,现在歇手了,在浦东置了一处房产,常年来回跑。又问起我熟人的熟人的一个孩子,当年同她有过联系;答说,很能折腾,干过跑堂,刻过图章,办过小报,做过生意,现在不晓得去了哪里,总归是折腾。
仍旧扯到文学。我说起年前读过的一篇散文,《芳草王孙天涯》,作者朱琦,讲的是民国达官贵人的后裔,如何在美国白手起家,低调做人,那里面就有她的影子,网上一索可得,不妨找来看看。她说“王孙”二字值得斟酌,有一股阿Q的味道,彼岸是前世,此岸是今生,来这儿等于脱胎换骨,一切从零开始,和彼岸的种种旧印记无关。说着就举出一位东北的学者,已经在大学做到副教授,敌不住外面的诱惑,来了这里,逾期不归,在餐馆打工,一干多年,他今生最宏伟的构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餐馆。还有一位,浙江来的,生物博士,高大英俊,一表人才,现在当导游,专门接待你们这种国内来的观光客。你不用哀叹大材小用、怀才不遇,这就是转世为人。
这期间她接了两次手机,听口气,都不是家里人。有一位像是国内新来的学子,询问有关上学的事……我于是把话题转到留学。她说留学是个机遇,美国有第一流的学科,第一流的导师,但是完成学业后,就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回去的好。在国内只要有一个平台,就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美国不是没有机会,如果碰上好导师,好课题,好单位,也会做出相当出色的成绩,但那是少数人,极少数人,概率非常之小。她认识很多专业人才,年复一年,只是在鸡零狗碎地打工,可惜了,也实在是浪费了。
既然如此,还是回国吧,至少可以让下一代回国谋求发展——我在心里说,不在嘴上,因为并不清楚她是否有子女,倘若有,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英文而外,是不是还会讲中文,是不是还对东方古国心存依恋……这将触及私生活的底线,打住。
尴尬。是我在尴尬。难道我和她真的已经隔世?沉默,姑且以咖啡当酒,干杯,干完一次再一次,咖啡味苦,全不似江南的清茶悦目,润喉,醒神。也许这儿正应了一句佛语:苦,才是人间正品。转眼看窗外,骤雨消歇,行人又开始招摇过市,片刻而后,我也将飘然远引……从兹一别,又将是海阔天遥,相会无期。当是之时,一杯在握,骨鲠在喉,我忽然冒出一个很乡气的提问:“国内人看美国,就像我们苏北老家看上海,一切都是摩登的,洋派的……但是我这次到美国,一路行来,发觉好多上了年纪的华人妇女,穿衣打扮比国内还土,一点不讲究,这是什么缘故?”她笑了:“你这是在说我吧。自古以来,‘女为悦己者容’,女人是为欣赏她的人打扮的呀。可是在这儿,有谁看你?谁的眼里又有你?日子一久,也就习惯了,麻木了,不再在衣饰粉黛上费工夫。”
瞧,说是不触及隐私,到底还是跨进了别人情感的领地——“这儿有谁看你?谁的眼里又有你?”致命的失落,绝望的苍凉,全在这一句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什么好问的呢?啊不,不,事情可以作另一面看。是眼前咖啡的刺激?还是多年清茶熏陶出的悟性?——我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好了,你现在可以当作家了!”声音之响,惹得邻桌的老先生侧身而睨。她先是一愣,抬头看我,见我一本正经,不像开玩笑,遂说:“你真是有眼力,这几年我一直在练笔,已经写了十多篇散文,关于我这个家族,关于我在美国的生活,其中有一篇,回忆长沙的,写到了你。”
唔,这番咖啡没有白饮,谈话至此,总算进入正题。文学是什么?文学是无线上网,是万有引力,是缩地术,心灵与心灵之间,总有千回百转万里犹面的机缘在。“我料定你早晚要回归文学,以前种种,都是铺垫,是爆发前的储备。”那一刻,我直视她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你应该放开写,文字绝对可以寄托生命,如果选择在国内出版,我可以帮你联系,另外,如果不嫌弃的话,我还可以为你的新书写一篇序——在这件事上,我自信比你身边的人更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