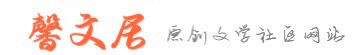一
从京南到京北,回程时我要转三次地铁。
转北京地铁十号线时,想起一首歌《十号线的忧伤》。我戴上耳机,闭上眼睛,让这首歌单曲循环。苏州街,海淀黄庄,知春里……巴沟。青年歌手花粥和四四在这首歌里,变着音调把这条地铁线上45个站名报了一遍。简单自在,懒懒散散像两只晒着太阳的小猫依偎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散淡地聊天。
简单到极致的歌词和旋律,却让每个听到它的人心头莫名地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我的思绪在密密麻麻的站名间穿行,回到了京南亦庄。已是耄耋之年的李博生先生鹤发童颜,气度不凡,声音磁性苍厚宛若远山悠钟。在袅袅檀香中,淡淡而忧伤地跟我讲:
“要说这些作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真想到世界各地找去。对于这件《伏羲》,我也曾在心里默默问过它: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你却认得我,
‘我少不得你,你却离得我,
‘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
李博生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文化部授予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他少年时就进入北京玉器厂学艺,曾先后师从中国玉器界“四大怪杰”中的何荣、王树森二位顶级玉雕大师。《伏羲》是湖北郧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请先生制作的一件镇馆之宝。
当我应云盖寺矿山公园之邀,前去看到《伏羲》的那一刻,就被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惊艳到了。《伏羲》的主题源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河图洛书”“伏羲造八卦”。整个作品线条圆润流畅、细腻饱满、疏密有致、浑然天成。背倚苍松的伏羲,右手执笔,左手拿着一卷半展的“河图”,“河图”上有只灵龟似在向伏羲翘首低语。伏羲的目光如炬遥望远方。脚下,一条巨龙捧着“洛书”盘旋而卧,仰首望向伏羲。细节处每一根发丝,每一片龟鳞都分毫毕现,而巨石、龙身、波涛则是挥洒粗犷的大写意,这和美术创作中“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理念很是相通。
当我追着伏羲的目光,我似乎看到了四海八荒山川大河。当我倾听灵龟的低语,似乎听到了周易八卦的神奇密码。我把自己置身于那巨石苍松之上,哦,我仿佛看到了宇宙银河,看到了历史的万古流淌。而承载这么多广阔意境的,只是一块六公斤左右的云盖寺绿松石那盈尺见方之地。
从青萍之末观天地万象。想起中国戏曲学院的杨菁老师由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处理,谈到文学创作的“时空意识”时曾说过一段令我们印象极深的话:
“舞台上,梅兰芳优雅地站在那里,‘她’就那么一站一望,说远处有山就有山,说近处有水就有水。‘她’还做了个‘卧鱼’,轻轻叼起了一支异香扑鼻的花,于是,那空空的舞台上,就姹紫嫣红满是花香了。”
这种具有“宇宙意识”的时空观念,在文学写作上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有了这种意识,可以让我们作品里的时间和空间都延展、丰富、灵动了好多倍。
果然,艺术都是相通的。
二
《十号线的忧伤》在循环播放,独特的京味儿,爱谁谁的腔调,一路喃喃自语般的碎碎念。一遍遍重复中不断跳出来让我心动的名字。
潘家园,十里河,分钟寺……潘家园是北京有名的古玩市场,也卖各种玉石。五年前上鲁迅文学院时,我和青儿常去那里逛。在那里我们看到很多卖十堰绿松石的,原石、首饰、各种手把件应有尽有。
绿松石虽是我家乡有名的特产,但生性素淡的我曾感觉绿松石太过艳丽耀眼而对它总是敬而远之。而在北京见到绿松石,却犹如他乡遇故知。在潘家园,我们看遍了青金石、墨玉、玛瑙、翡翠、和田玉一众玉料之后,再回转去看绿松石,感觉她是那么独特、亲切和美丽。

绿松石因“形如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绿松石的颜色可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绿”字来概括,而是由绿、蓝、黄三大色系形成绚丽多彩的松石色谱。单说她那“绿”的色系吧,就有草绿,军绿,蓝绿,油绿,苹果绿等。还有一种绿中泛黄的“菜籽黄”,也有十几种不同的色彩。在绿松石中,蓝色系的色彩变化之多更是令人心醉,再加上绿松石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铁线、伴生矿点饰其中,它的意趣就更是富饶了。当你走近绿松石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它的艳而不俗,雅而有趣。每一种色彩的变化都很有妙韵,或盈绿或晕黄或沁蓝或飞墨,或深或浅,像一个灵动多姿的女子,风情万种,丰富而有趣。如果绿松石的“绿”代表着青山和碧水让你赏心悦目的话,那么绿松石的“蓝”则代表着蓝天和大海让你心旷神怡。在众多矿口出产的原料中,云盖寺矿出产的一种深蓝色绿松石因为质地细腻、色泽亮丽,碧如蓝天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云盖蓝”,是世界公认的松石极品。
当我问及李博生先生对云盖寺绿松石的印象时,他用很诗意的语言描述:“‘云盖蓝’是松石中最为高档的玉料,那如同蓝天一般的颜色,被称为‘天空的石头’,再加上那些铁线的对比,像一个少女穿着婀娜飘逸的白纱,缓缓行走在月光下一般神秘而空灵。无论是玉的主人,还是制玉的匠人,和这般的松石玉料相遇,都是要缘分和福分的……”
我和青儿每次在潘家园里一逛就能逛大半天,主要是看绿松石,听店家讲绿松石,对比每家绿松石的价位和石料。末了,两个人总会收获几样喜欢的绿松石小玩意儿。此去经年,每每看到绿松石,脑海里就会经常出现暮色中我背着一个花布背包从潘家园回到鲁院,一路上心里都喜滋滋地,像小时候兜里揣着几颗糖回家一般欢喜。于是,对松石的喜爱便有了来自两个城市的记忆,还有和另一个女孩儿一起寻石的快乐友谊。
在家乡时戴绿松石其实是不多的,但这两年在北京的日子里,出门佩戴最多的却是绿松石。有一次聚会之前,朋友很神秘地告诉我会有两位十堰老乡参加。那天我戴了一串我自己设计的细密雅致的绿松石手链,有一个女孩儿戴着一条自由而大气的绿松石随形毛衣链,虽初次见面,但绿松石犹如接头暗号。
我们相视一笑,嗯,确认找到同类。
三
惠新西街南口、芍药居………
耳机里,花粥和四四又一次唱到这两个地铁站名,这是我在北京最早记住的两个站名,那是鲁迅文学院附近的两个地铁站,是我和同学们每次外出与回校时的必经之地。
在这座文学的殿堂里,我们接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文学撞击。《永远的文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俄国文学地图》《文章为美而写》《我的散文观》,每位老师都手拿着一把“手术刀”,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全新的“解剖”手术。“解剖”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一头雄师,一只麻雀。我看到触须的颤动,肌肉的纹理,血管的蜿蜒。
一次次文学沙龙、作品研讨、小组讨论,社会实践,热气腾腾,烈火熊熊。置身其中,即使我一言不发,趴那儿不动,也会被嗖嗖扫过的子弹击中,而那种被击中的痛感是如此快意,令我一次次惊悸和觉醒。
这四个月的火种,将为我们抵御未来四年、四十年的风雨严寒。
但有位老师也曾意味深长地提醒,你们用了四个月来走进鲁院,将来可能需要用四十年来远离鲁院。
矛盾吗?并不。
关于“走进”与“远离”的问题,在李博生先生这里也给了我很好的答案。
先生是制玉大师,也是善于思考和传道的一代“哲匠”。他说:“制玉的八字方针是‘量料施工,因材施艺’,制玉的两种境界是‘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
“我跟随师父了十几年,自己制玉六十六年。但人生大多数的时光都逗留在那个‘必然王国’里。比如说做一尊观音像,师父说了这观音的脸是坠子形,五官呢,莲花眼、柳叶眉、玄丹鼻,五个梅花瓣的唇结,微笑的唇型,这都是定下来的,这叫必然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师父教的我都掌握了,曾经很是自得。在‘必然王国’里,你会觉得很舒服,觉得这就到头儿了。
“而到了我45岁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想从那个‘必然王国’里逃离,进入到一个‘自由王国’再进行创作时,就找到了师父当年说的‘看到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东西’的感觉。
“比如做一条龙。一条龙它是怎么个型,那是人想象出来的,但你不能瞎想象,首先得从传统中来,历史上的龙是什么样子,汉龙什么样,清朝的龙什么样,这就是‘必然王国’。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认识、融合与创新,闭上眼睛,一条属于你自己的龙在你眼前就出来了。这就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
纵观李博生先生《人之初》《禅》《鼓上飞燕》《十八罗汉》《伏羲》等诸多传世之作,都具有“自由王国”制玉的气质,有来处,有传承,又融合了个人的思考和创意。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必然王国”是“自由王国”的基础,只有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才有底气和能力自由挥洒策马驰骋。
写作也一样。我们向大师靠近,向经典学习,多读多写多思考,打下坚实的基础,但要有警惕心,不要失去自己。就像孩子学习走路,不可能永远牵着大人的衣襟,要学会独立行走,要去寻找属于自己通往远方的道路。这时的你,会有意慢慢远离那些大师,找到重新诞生的自己,才能进入写作的“自由王国”。
四
知春里,知春路。
“东风归来,见碧草而知春。”在这《十号线的忧伤》里听到这两个站名,依然觉得如沐春风一般美好,眼前会有一条在春天里不断向前延伸的大路,两旁绿柳摇,一望春深处。五年前,我从北京知春路地铁站出去,走到中关村里的一栋住宅楼里,看望一别七年的吴新智先生。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屋子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的书籍,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窗口摆着两排花草绿植的木桌上,然后又从那木桌流淌到下面的茶几上,那上面的一堆资料旁摆放着两具头骨标本。若是在别处忽然看到那头骨,定是令人毛骨悚然,但放在吴老的屋里,一点也不令人害怕。
吴老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世界有关现代人起源两大学说之一的主要创立者,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虽不从事文学,但国学功底很是深厚,博学多才,也会每每问我,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没有啊?若读我的小文,他都会认真回复,并对其中不妥之处一一列出,大到立意和结构,小到字、句、标点,都会耐心交流和指导,严谨的精神和对晚辈的爱护令人感佩。
五年前已经89岁高龄的吴老,思维清晰,十分健谈,仍然在坚持学术研究,我去的前几天还在接受澎湃新闻网的采访。说起我的笔名“李小奔”和七年前他赠我的话——“集腋成裘,随遇而进。”吴老从书柜里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科学的道路》下卷,翻至某一页,微笑着递给我。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生平合集,那一页上吴老的自传标题正是“集腋成裘,随遇而进”。喔,原来这句箴言凝聚着老先生几十年人生经验的智慧“舍利子”,这是多么宝贵的人生加持啊。
我的笔名,也是从这两句话中诞生的。清醒坚定,慢而不止,小奔也。
那天照进屋里的阳光,还有阳光里坐着的那位老先生都如春天一般温暖。
如是斯年,故人远行。2021年12月4日晚,吴老为自己此生的行程画上休止符,享年93岁。他睿智而慈祥的笑脸,永远定格在知春里那个如春天般的冬日。直到后来我看到他的学生吴秀杰告诉《中国科学报》:“吴老师对学生总是爱护有加,倾囊相授,极有耐心。他特别喜欢我们问问题,他会摆出他的各种标本,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会厌烦。收到学生的文章,他批改得也格外认真,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也不会放过。”
是啊,如此看来,我也荣幸地算是先生的一个编外学生了。
其实吴老是想带更多学生的。自2000年后,吴老在科研之余还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科普工作,作报告,开讲堂,进校园为中小学生做科普公益讲座,还为青少年撰写出版了《人类进化足迹》和《探秘远古人类》两本科普著作。这种传道授业的精神,实在可敬可叹可爱。
李博生先生的话亦如金石声:
“国家授予我‘非遗传承人’,这不是头衔,这是我的责任。那我就得把当年我的师父教的我制玉手艺,加我的认识,再教给下一代,这才叫‘传承人’。不但要传承,还要守正创新,中国的玉文化一定要培养出四种人——玉文化的艺术研究者、玉文化的科技人员、玉评人,还有能做玉的,有哲学思辨能力的‘哲匠’。”
李博生先生甚至想去出家做和尚。他愿意做一个“试验品”,做第一代“玉僧”。他想把做玉的手艺带到庙里,带进佛家,让那些在寺庙里的小沙弥们除了上早课、晚课之外,能够学到一门手艺。
“我恨不能把我的肠子拿出来量量多长给世人看。”
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玉文化行列,他想在这里头发现做玉的人才,把一身的手艺传给更多人。
一个是研究古人类学的科学家。
一个是玉器界的工艺美术大师。
他们做的工作半分都不相及,没有可比性。但是其传道授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何其相似。
何为家国情怀,何为知识分子,何为真正的大师。
如此,是也。
五
牡丹园,健德门,北土城。
“乘客朋友们,下一站,北土城到了,要换乘八号线的乘客请做好准备。”
地铁里播音员的声音刚落,要在北土城下车的人们纷纷朝门口聚去,车门一打开,人潮立即像一群鱼儿逐食一般涌向自动扶梯。面对汹涌的人潮我总是心生恐惧,不喜欢被裹挟着前进,也不喜欢争抢。我侧身往边上让了一下,跟随着人群的尾巴上了自动扶梯,自觉地站在扶梯的右侧。随着扶梯的缓缓上升,我的目光逡巡了一遍这个站内四处古意盎然的青花瓷装饰。
北京的地铁实在是可爱,除了通达度很高以外,还将每个站点的装修与周边环境相结合,形成了“一站一景”的地铁文化。北土城站外面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所以具有中国古典之美的“青花瓷”是这个站的主题元素。站台上,白底蓝花儿的青花瓷高大圆柱分列两旁,屏蔽门、楼梯墙面和指示牌上也都贴着各种青花瓷图案。
我从地下二层的十号线站台,走向地下三层换乘八号线,这条线通往我在北京暂居的小窝。
梅花、兰花、中国结、龙、赛龙舟……满目的青花瓷从我身边走过。在我的脑海里还掠过地铁6号线杨庄站“燕京八景”里北京的妖娆冬色,田村站似梦境般空灵的壁画《白夜鹿语》,7号线珠市口站内壁画上北京城南的胡同往事,旧城繁华的“流金岁月”。虽然人们行色匆匆,并没有多少人去用心留意这些。但做的人都是无比用心。而且不管你是否关注它,它一直都在。当你经过时,它带给你的那种独特气息也一直都在。就如同你从一个花园经过,不管你看不看那些认真盛开的花儿,那花香,那些花儿带给你经过时的美好都在。
是呢,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傻傻地坚持做一些并不被世界关注和重视的事情,或者说是在做一些小众的,甚至有时被人们看作“无用”的事情。
我问李博生先生,想要成为制玉高手最重要是一点是什么。
大师说:“玉汝于成。最重要的是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一旦坐下面对一块玉料,就要把自己心里那些要挣多少钱啊,要得什么奖啊,各种起伏纠结的情感啊……所有杂念全部清空,然后装进正念。这个正念很简单,就是要做一件好作品。如此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去切、磋、琢、磨每一块玉石,同时也在切、磋、琢、磨着自己的技艺、精神、品质和胸怀。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琢磨中,孤独已不再是孤独,寂寞更不再是寂寞,它们就会成为你最为亲密的朋友。在这时,你因为纯粹而自在,因为自在而自由,真正达到一首禅诗所言,‘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写作,门外的繁华,已不再是我的繁华。我爱这文字中的世界,在这个文字的世界里不断奔突、跋涉、跌倒、探寻,又不断清醒自视,倔强站起,坚定地前行。没有一个文本会是十全十美的,每一次写作都是新的开始。我从未长大,但我从未停止生长。
采访快结束时,由《伏羲》问起李博生先生其他散落在世间的传世之作。先生的声音忽然有了一些沙哑:
“虽然是我亲手把它们做出来的,但百年以后它们还在人间摆着呢,而我早没了。是不是有一点伤感?”
我点点头。又望着窗外一排幽密葳蕤通往夏天深处的栾树,笑着摇摇头。不,换一个角度想,那些作品是您生命的延续。您的精神和意念和它们已经融为一体,就像是您的孩子。它们分散在世界各地,那您在世界各地就有很多个孩子啊。一个人的生命还能有这样一种存在的方式,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先生略有所思,点点头。
“嗯,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伤感,是很庆幸的对吧。我很感谢你。”
……
回想间,八号线地铁已经来了。